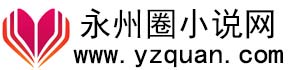30-40(29/34)
年的心情,很疼吗,害怕吗,还是想念呢……谢景珩脑子里昏昏沉沉,经常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两年前,分不清人生这几段,哪段是真的,哪段是梦。
他不知道怎么醒过来,却经常无意识摸身上的管子,没有力气拔,也经常掉眼泪,疼的。
那天夜里他疼醒的时候,江浔正在给他擦眼泪,看到他醒了“唰”地睁大了眼,按响呼叫铃。
江浔还低声和他说了两句话,说的什么他听不清,耳朵和周围像隔了层水膜,好大一会儿才消散。
医生很快围过来给他做全身检查。
他带着呼吸机,说不了话,眼睁睁看着医生翻动他的身体,哪都动不了,一直检查到腰上,他才有感觉。
上肢还能控制,但手指握力很差,虽然医生说是暂时的。
惊奇的是,检测结果显示肌张力恢复了,至少是二级。医生问他有没有感觉,让他尝试控制,他只能眨眨眼。他感觉不到这件事的用处,也依然感觉不到那部分身体的存在。
有感觉的部分很疼,到处都疼,撑过检查完那一阵他就又晕过去了,什么都没来得及想。
后来醒也是断断续续的,叶青予和叶青梨来看过他,大部分时候病房里只有江浔,有时候用棉签给他在干裂的唇上沾点水,有时候在跟他讲话,有时候在忙工作。
只有江浔在的时候他才觉得,他并不在那场车祸后。
第四天上午,他意识完全恢复了。
不过他猜测是医生减了麻醉剂量,因为那天开始所有疼痛更尖锐地传递给大脑,有种麻药劲儿过去的感觉,又清醒又痛苦。
骨折的肋骨无时无刻不在疼,每呼吸一次都能感觉到。
哪的骨头断不好,偏偏在身体仅存的感知处,巴掌大的地方,痛觉被无限放大。
呼吸机插得他喉咙痛,被这东西控制呼吸频率也很难受,简直是折磨。
没日没夜地疼,醒了还不如不醒。
他醒的时候江浔一直是醒的,江浔什么都不问他,只是工作上的、生活上的事都和他讲,他从来没见过江浔这么多话。
他一般胡乱眨眨眼回答。
早知道会醒过来,当时,他就不亲了。
他不清醒的时候,大抵也是江浔照顾的。
只是,他还没想好怎么面对江浔,至少清醒的时候很难接受江浔给他做护工干的那些事。
他面对这件事忍不住发怂,但毫无办法。
能不能晕过去算了……
“身上还疼是不是,再坚持一下,一会儿叫医生把呼吸机摘了。”江浔很轻的握着他一只手,按按他泛红的眼角,恨不得替他疼了。
江浔没骗他,当天晚上医生就撤了插管式呼吸机,换了鼻罩式。
“可以说话吗?”江浔紧张地问。
谢景珩张了张嘴,嗓子疼得一股铁锈味儿,“能……咳咳……咳……”
半个音节哑在嗓子里,只剩断断续续的闷咳,他腹部发不出力气,除了那点血腥味什么也咳不出来,反而牵动了肋骨的伤。
“没事没事,疼就先不说。”江浔把他半揽进怀里,顺着他胸口。
怀里的人脊背瘦得硌人,细微地发着抖,睫毛随着胸口的震动轻颤。
江浔等他呼吸稍微平稳了,想再扣上呼吸机,却被谢景珩用手拉住了。
冰凉的手指没几分力气,江浔反手握住他。
“我不想戴…也睡不着,能不能…扶我坐一会儿……”谢景珩喘不上来,一句话说的断断续续